剧照
剧情介绍
安妮特电影免费高清在线观看全集。
讲述一对好莱坞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安妮特的故事:丈夫亨利(亚当·德赖弗 Adam Driver 饰)是一位单口喜剧演员,妻子安则是一名歌剧明星(玛丽昂·歌迪亚 Marion Cotillard 饰),而他们神秘的女儿安妮特,又拥有怎样不同寻常的人生呢?陌陌影视陌陌影视樱花影院6080影院路易之后美食、祈祷和恋爱阿兰布里斯塔听说很好吃第四季冰血暴第四季金手指2003那时的我们养鬼吃人5三体第一季未来中国王者后羿夏洛克的孩子们电影版冤家搭档 第一季古宅老友记第二季爱的着陆民国奇探致莱斯利时光与你都很甜速看版完美嫁衣寻龙宝藏芳心他属了不起的盖茨比1974火弹行动神探南茜第二季火星异种
讲述一对好莱坞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安妮特的故事:丈夫亨利(亚当·德赖弗 Adam Driver 饰)是一位单口喜剧演员,妻子安则是一名歌剧明星(玛丽昂·歌迪亚 Marion Cotillard 饰),而他们神秘的女儿安妮特,又拥有怎样不同寻常的人生呢?陌陌影视陌陌影视樱花影院6080影院路易之后美食、祈祷和恋爱阿兰布里斯塔听说很好吃第四季冰血暴第四季金手指2003那时的我们养鬼吃人5三体第一季未来中国王者后羿夏洛克的孩子们电影版冤家搭档 第一季古宅老友记第二季爱的着陆民国奇探致莱斯利时光与你都很甜速看版完美嫁衣寻龙宝藏芳心他属了不起的盖茨比1974火弹行动神探南茜第二季火星异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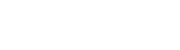
看的时候想了无数次,这也许就是舞台音乐剧和音乐剧形式电影的壁垒,而卡拉克斯是想要打破它。
卡拉克斯叫我们禁止呼吸,因为不然,我们会发现自己无法喘息。一部美国电影——被诅咒的电影,“历史的最后一章”,卡拉克斯恢复了一些古老的东西:美国电影的线性时间,不可逆的,因此它不可能如奥斯卡先生一样在无限宇宙中超越生死,而必须是Adam Driver,大明星走向金·维多《群众》和斯蒂文森《郎心似铁》结局的深渊;一部法国电影——被消失的电影,卡拉克斯又带回了一些古老的东西:法国印象派电影,让·爱泼斯坦的鬼魅、阿贝尔·冈斯的叠影、路易·德吕克的树、雷诺阿的戏台,一起掘出这最可怖又动人的坟墓。
一头一尾,从“May we start”到“Do you like it”,卡拉克斯的作品依然以强烈的自反的姿态带领我们体悟电影本身与表演本身的意义。红黄绿之中的颜色编码、反复出现的苹果意象和这次“水”的元素等等都让人忍不住反复去揣摩他的用意。它本身的结构十分工整,文本层次却极为丰富。视听依然是一流的,叠化转场取代跳切和升格,成为他最新的语法元素,更添鬼魅气息。
司机演的还行,唱的真的是折磨我的耳朵。我跟卡拉克斯还是挺难connect的,这位特有范儿的,少年时期喜欢骑着摩托车刺破巴黎郊区宁静的来自巴黎富人区的白男导演,感觉一辈子也就爱讲一个优越文艺白男自恋刻奇的人生。年轻时候是谈恋爱,老了开始讲女儿,但翻来覆去中心还是自己。连女儿都不是女儿,是个木偶,很creepy哦。蛮过时无聊的,但我也从来不讨厌卡拉克斯,真有范儿,但你让现在的我去跟这样不肯老去的倔强老男青年喝酒听他吹b,我可能也不会了。
歌难听,娃娃丑,故事无甚趣。
电影没啥问题,但歌真的难听,二元共存太难了,耳朵想谋杀眼睛让我打0星。
失望透顶,卡拉克斯生涯最差。只有片头声音提示与片尾落幕散场的自我包装是成功的,那是属于第一段人声录音、马戏团、傀儡剧目、村庄戏台与爱伦·坡的历史墓穴中的观看与聆听,但电影并未变成期待中的穿梭在旧世界与新世界之间的神秘演出。简单的寓言故事,成为最直白的视听风格组合排列的白色画布,然而既往的模糊掉人类语言意义和社会行为的如怪物一般仅能靠观察与想象来透视的的奇异影像,在歌舞片与英语系的通俗规则下却反生出了巨大的限制和枷锁。披上绿色睡袍的德赖弗,与歌迪亚间展开的不仅仅是一段《黑猫》或《泄密的心》似的哥特情感怪谈以及卡拉克斯的回顾与忏悔,更是古典法国电影与现代美国电影的奇妙联姻,然大师技法和名作段落的复现,却总在一种过犹不及的冲撞下局限为最无机的油彩斑点,并未流动、浸染与融合,在形式的漩涡中淹没沉沦。
总的来讲失望成了一个球
故事简单对于卡拉克斯本最不是问题,形式的、修辞的拉满即可。但《安妮特》在视听层面的捉襟见肘感太强了,音乐、哥特式人物和场面塑形皆是点到为止,没预算惊世骇俗,但天马行空棚拍总可以吧,没有都没有,好像钱都花在台下群演身上。虽然不至于又臭又长,但也真的乏善可陈。 @望京电影资料馆
瑰丽大气的影像,转场如动画般的朦胧,adam driver的演技已经不需要证明了。故事则设计得很套路,一切为了催生情绪的起承转合,结尾小女孩演技不足以撑起这个本该肝肠寸断的画面,脸上滴的眼泪和木然背词的表情没办法共鸣。(还不如不换演员呢,虽然也是一种情节必需)
3.5-;Henry形象塑造的别扭(除了告别演出和观众对峙那段拍挺好,余下心理层次的转折都颇为古怪)和与之对应的舞台化人物设计,才是影片在两种艺术形式间来回冲撞、情感支点松垮的源头,而非那些跳脱的布景和唱段,由此也削弱了鬼魅外壳下深沉的思考性,使得整个故事被陈旧寓言的巨大惯性所制约,滑向某种模式的勾勒,全靠Carax天才般的视听创造力才能将人摁在屏幕前。然而炫目的形式杂耍更多也仅止于拼贴和涂抹,未能如以往构建出一个自由狂放又引人深深着迷的世界,此刻再去挖掘当中隐晦而犀利的观点表达,也成了件勉强的事。
Carax和女兒 Nastya 站在一起,送別男女主角到戲情裡去,今次的自涉會不會過份明顯?總是想到Yekaterina Golubeva身影,老靈魂突如其來之死是否與Carax有關,好幾幕Cotillard 如鬼魂一樣撲向主角, 蕩樣在電影中的回音是兩人關係的種種陰影?這位愛吸毒又暴躁的生活實踐者交出的盡是悔疚,暴裂與溫柔的男與女相遇套路也不再浪漫,連女兒都要活起來與你告別,「再不會有人愛你,你沒有人愛。」不懂愛也不會生活的惡魔寫照,一百三十鐘講自己是一個怎樣仆街,太沉迷於角色病態一直是Carax 的死症,但電影創作也不是治療,那是快要好才能可以交出的功夫,那是痊癒前的大口呼吸。是宣告沒有人愛的人都留在電影世界好了,幸好,你不用留在這片世界裡,最後與女兒和伙伴遊歷百鬼夜行來祭禮。更喜歡Holy Motors 裡與Denis Lavant一同投入各種不同生命可能。
做爱的时候就不要唱歌了吧(
(7.6/10)《安妮特》是Carax作为父亲写给女儿的道歉信,同时也揭露了《神圣车行》留下的开放式结局:Oscar先生最终也成为了一名礼宾车司机。《安妮特》延续了《神圣车行》的怀旧主题,它是Carax对逝去感情的怀念,以及对过错的愧疚和悔恨。电影中出现的绿色是主角Henry(也就是Carax本人)的颜色,代表了导致他犯下错误的自私、自毁、怀疑和逃避。本片类似林奇和德米的结合体,但情绪大于情感,不加克制的情绪让电影看似很满实则很空。不过话说回来,创作者也有表达私人情绪的权利。
4.5,卡拉克斯的影片一如既往地充满巴洛克色彩,如同他十年前的《神圣车行》,开场的画外音与麦克风声音作为电影本体=催眠术的隐喻,恰好并置于亚马逊的logo——剧场。在影片之中,一个情节剧叙事在歌舞剧唱段和林奇般的柔化叠印中变得诡异化。《安》是查泽雷式复古歌舞的反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将现代性引回古希腊的诗学之中。安妮特是一个能够引起恐怖谷效应的人形,是Henry(摧毁,酒神精神)与Ann(建构,日神崇高)失败的交合的副产品,她的别名叫做资本,而影片则是一个黑色的《木偶奇遇记》。正如同在恐怖影片中所看到的那样,这个鬼娃占据了”Ann'之外不可化约的残余,并在沉默中发散出的强度导向了一个巴洛克色彩的全球叙事/分裂/剥削三位一体之中,一如斯洛特戴克通过球体理论对于全球化进程的重构。
很诡异的片子,很诡异的故事。前半段让我想起《纽约提喻法》,后面情节完全失控了。Adam Driver的角色第一次在舞台上发疯的时候就奠定了之后的基调:从导演到演员,谁都不知道到底要表达什么,倒是群演信念感很强,因为他们就按传统musical来演的。(而导演和两位主演对旋律都不敏感,不知道为什么非要选择musical这一形式,暴露自己的短板。)一出credits我身后有个观众就迫不及待地说:I'm so confused。
基本元素集齐,众人捧高的时代,美誉总是不缺。故事本源,剧作结构/叙事的平凡普通,时间线成长的庸俗,主演的努力,剧情片音乐剧互融的各种寡淡浓香的尝试,皆见。符号时代已经过去了,硬搬概念以为再创新没那么简单。可有些声音和喜剧/歌剧场面(bob wilson的版权费怕是付了不少?)真的是勉强亦无利,与剧场人而言只是抄吧。同时,音乐的轻佻和套路让人无法自欺。木偶的缺钱做作,真小孩的尴尬大人演法亦让人思绪冲突,无法一口咬定导演的真身究竟有几成。最最末尾,还不忘叫观众喜欢记得告诉朋友,那不喜欢,也一定要告知吧!另,苹果和香蕉已经不是隐喻了,是明喻。metoo还不忘晃打一掌,编剧实质对男主充满了同情,女主天使降世一样的唯美空白以及鬼混乱入这些都…………还有就是LC在这剧本里多少投入了自己的生活情感???
没爱也没恨,没导也没演。打破但没建立,全程死而不僵。2022.01.08 法文二刷。确认了,作曲没啥问题,就是唱得太差了,上气不接下气的。
今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获得者,原来是三十多年前因为《坏血》、《新桥恋人》等片轰动影坛的法国新浪潮后代表人物卡拉克斯的新作。采取音乐剧形式的剧情片,视听制作、运镜调度依然够质量,只是其内容苍白,无趣。导演有61岁了吧,还不老啊,应该有更出色的表现!
Pure cinematic experience。开头一个长镜头从现实直接转入电影,太妙了!故事是薄弱,但这不是问题所在,我从来都偏好故事相对薄弱但能给导演留下更多发挥空间的电影,但是这一部怎么说,故事-形式构架中空了,该放进去的东西或者说要表达的东西(情绪?好像卡在某个地方没有进到电影里去也没有从电影传达出来。尽管如此,你不能否认被那些纯粹的cinematic moment击中时、不知道该做何想法时的无措所带来的悸动感,这正是卡拉克斯的魅力所在,也正是电影作为完全视听艺术的魅力所在。P.S. Simon Helberg in,Adam Driver out。